歐斯華(Alice Oswald)出生於1966年英國一戶貴族之家,熟習古典文學的同時,也極善園藝,這使她的寫作狀態非比尋常。2019年,她獲任牛津詩歌教授,成為此一職位的首位女性。早先,她曾四度入圍英美最負盛名的艾略特詩獎,並於2002年以詩集《Dart》得獎。歐斯華長駐「達特河」三年,描述河的生態,及河上生活的人物,視角層疊而廣張,包括博物學家、漁夫、錫礦工、林務員、游泳者、污水處理工、造船匠、採牡蠣人、擺渡人、海軍學生、領航員、海豹觀察者等,不勝枚舉。2019年出版的《無名人》,也呈現了這種複眼特質,不過詩中的故事背景不再是物質的河流,而是口頭的、時間的、話語的河流──史詩。
坂本龍一曾說專輯《async》是他想像中一部塔可夫斯基電影的配樂,換句話說,這張充滿了環境音、物質感,同時展現實驗電音的專輯,誠懇而激越地,「投射」出了一部不存在的,想像中的電影。而這正是我讀《無名人》的感受。
歐思華以《奧德賽》背景中的一片大海,區隔了「放逐孤島的詩人、返航的英雄丈夫、密謀殺夫的人妻」等三組主要角色。藉由多組視角的來回橫跳,古典的大敘事,恍如一逕摔碎在了堅硬的波濤上。如此,大海化為一座「環形散景幻燈片」,一面蛛網破碎的鏡子,投射出了月的暗面──另一部水面下的《奧德賽》。詩中各組人物,在大海的阻隔與包圍下,既無法看清對方的局面,也無法認清自己的命運,一貫是困在自我的呢喃與徬徨中。我將這樣的視角,理解為詩人一開始即已設定的「散景」,又稱為焦外:鏡頭在淺短的焦距下(角色困於自我無奈的微觀),使被攝物(遙想他者的情節)落在景深之外,產生寬鬆、斑駁、混沌的絢麗效果,卻也凸顯了人與人之間,荒蕪的隔閡:
這麼說吧我不以為一個人
溺死或從這無垠的馬賽克再浮起來
我不以為他能
聽見我們
全詩共六十四頁,每一頁如同一片波浪,長短不拘,甚或單行成頁,雷同的句式亦疊章複現,此外還夾雜了不少空白頁──或平靜或激動的浪花。由於每一頁詩,都被假定為一片浪,而浪花從不單獨出現,總是結伴而行──詩行篇章前進的勢態,不可避免地呈現出:沒有先後、沒有主次、沒有因果。這正是閱讀海浪的困難,也正是閱讀海浪的愉悅,向觀眾拋出了一道詰問:這裡一切都會消逝,這裡沒有人,除了豐饒的細節,你還想知道些什麼?
我們實在很難知道更多。海上日夜難分,生死交會,溺斃揮舞的雙臂,竟像是歡心的舞蹈,令人蒙昧又沉迷。我們想看清水下的事物,卻只見泡沫不斷湧升。水下是亡者的世界,由一片昏黃所包覆,亡者只能繼續勞動,假裝自己並未身死,「保持動作超越那彷彿無盡的昏黃」。我們凝視水下,彷彿望入深空,卻飄滿了星際懸浮物,「只要那遠古的星宿依然維持精準方位/依然確實渴見卻不十分確實//是啊水底仍然若有似無隱約」。水下是深淵的紫色,是疲憊的神,聆聽上方浪花兇惡,將死之人在心中呼喊,向命運回絕:「別/別是/我」,隨即超越意志的潮浪將他溺斃。水下,就連詩人也無能為力,彷彿一隻章魚:
帶著空空的吸盤
在海面匍匐膝行
我已失去了一切甚至失去了重力請憐憫我
當人妻閃躲著詩人的監視,詩人閃躲著海鳥,而海鳥暗示著無數亡靈的變形。成群的海鳥,莫非是高空中,排列字幕的無人機?海鳥活在世界凶惡的邊緣,叫聲讓人一瞬想及靈魂深邃的悲哀,穿梭現實與想像之間,橫越一座座心的孤島。一切險峻與美麗,環繞、包圍、滋養著牠,使牠顯得比神更疏離,也比人更聒噪。
與此同時,詩人、英雄、人妻,至始至終,仍困在人性自我的海島,兀然生滅,但願自己身在他方「那邊」,卻離不開島,化不為鳥,只能坐等命運的到來,將他們擊落海底。
海作為液態的鏡面,具體而又寫意,投射了一切:它既是傳聲的媒介,又是隔絕的天險。海同時是人心的焦渴,無意識的瘋狂,同時又是合唱隊的旁白,神的悲憫與調侃。海是內在的具現,又是現實的布景,是藍色的盲眼,又是某人的裙擺或床單。它既是床鋪,也是一場夢本身。它彷彿全知,卻又僅能映照出偏僻的一角,「被光線切割的層層/視覺帷幕下它依然//完整」。
最後,貫穿全詩的紫色,究竟代表著什麼呢?紫色,是藍與紅的調和。換句話說:是血融於海,而尚未消褪的顏色。是人性愛恨,落入荒蕪宇宙,而一時留存。紫色一貫是帝王,英雄,聖人的顏色,而在剎那的搖晃後,又回歸為一片碧藍冰冷:
繆斯啊跟我說說這古老的旅人吧
他發現自己漂流在無底的空間
數不清的星球圈圈環繞他
一如諸神無所事事
所有的光與無光他一一見證
作者簡介
延伸閱讀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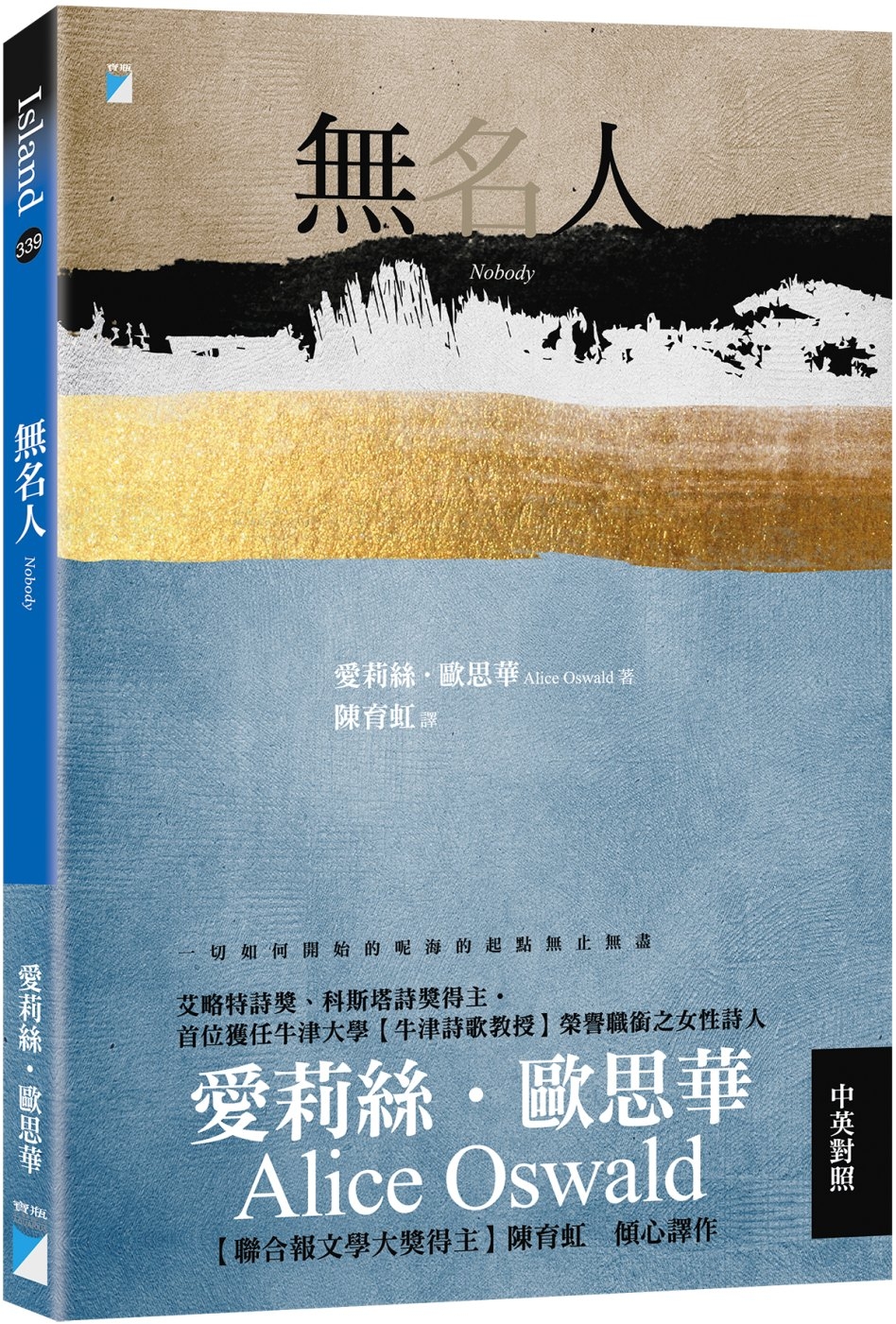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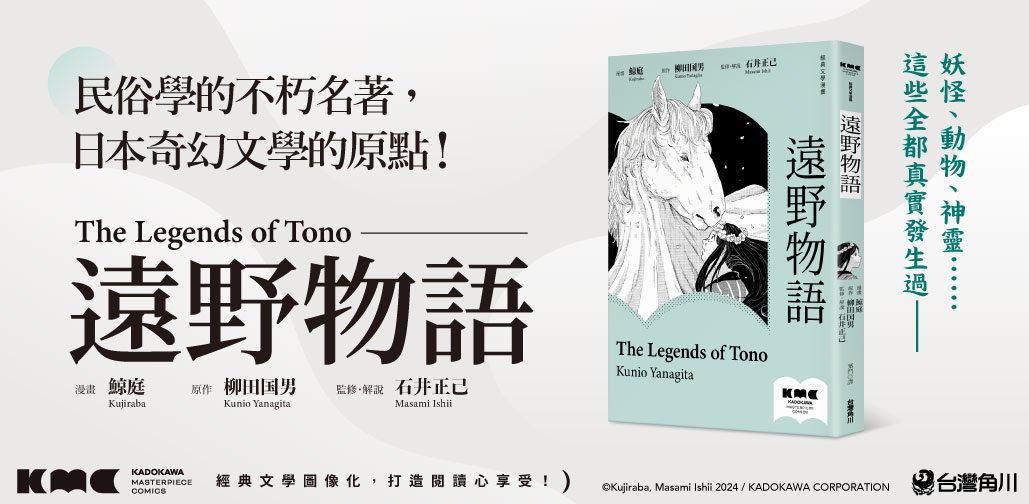







回文章列表